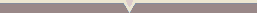谈到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人们立刻会想到她是一位通俗作家,认为她的作品缺乏文学价值,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常常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有时出现偏颇的例证,而且她还曾被指责是个反共的反动作家。那么,为什么要翻译出版她的作品呢?从出版角度考虑,既然准备出所有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的作品,自然不应该把赛珍珠排斥在外,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她在一九三八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是一套丛书的完整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无需多加评论。至于从作品本身来看,有没有出版意义呢?我的看法也是肯定的。这里包含一个对通俗文学的文学批评问题,也包含一个如何对待作家和他的作品的问题。
毋庸讳言,如何看待通俗文学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存在着争论,我无意去评论各种不同的意见,这里只想结合国外一些文学批评理论谈谈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个人看法。
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饭店看一位美国朋友,闲谈之中,他妻子问我:“你读过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吗?”当我告诉她不仅读过,而且还在翻译时,她高兴地对我说:“我对中国的兴趣就是从读那本小说开始的。我是在上大学时读的,从那以后,我非常注意中国的文化,而且一直想到中国来,直到最近才实现了我的愿望。…·我和我的许多朋友都喜欢读她的作品。”这位朋友上过大学,现在协助丈夫搞商业工作,在美国属于占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我认为她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阶级广大妇女的看法。
一九八六年我到美国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有意了解了一下赛珍珠作品的借阅情况。根据洛杉矶和厄湾两个加州大学图书馆借书登记,从一九八O年到一九八六年平均每年有七人借阅《大地》,在一殷小说中可以说居中上地位。至于借阅者的背景,我无从知道,但至少应该是大学学生。根据这个数字推算,赛珍珠的作品在美国仍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人们预计,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她的作品会有更多的读者,因为毕竟她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妇女作家。
以上两个事例说明,赛珍珠的作品,尤其是《大地》三部曲,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她的作品呢?
毫无疑问,《大地》三部曲属于通俗小说,赛珍珠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点,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追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有些看法和资料并不完全正确)以后,公开宣称“立志不去写那些漂亮的文字或高雅的艺术”。但是,通俗小说毕竟是文学的一个门类,如何认识,如何评价,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新批评开始,西方的文学批评一直强调作品的本文研究,不论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把作品的社会性抛在一边。这些理论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对文学批评的发展也确实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毕竟基本上只限于学术界和大学的范围。今天,分解主义(Deconstruction)在美国巳流行十多年了,但你若问问人文学院以外的学生甚至教师,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不知所云,即使在人文学院内部,也只有文学和哲学两系搞理论研究的人比较清楚。至于广大群众,可以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这种脱离社会的研究引起了许多批评家的反思,因此在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学派——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把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统统纳入历史的范畴,从历史的发展中来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这一学派指出:一部文学名著是各种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几十年来的传统看法则认为它独立于社会之外。这就对一部文学名著的价值超越时间和地点的看法提出了跳战。正如美国著名批评家简·汤姆金斯在她的新作《感人的构思》(Sensational Designs1985)一书的前言中所说:
“这是一种努力的开始,努力把美国文学研究从过去三十年来统治美国文学评论的一小部分名著转移到一种更丰富多样的研究领域。它…·包含着一种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因为它不是把文学本文看做以复杂形式体现永桓题材的艺术作品,而是把它们看做一种重新解释社会程序的努力。根据这种看法,对小说的研究不应该因为它们成功地避免了它们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局限,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文化对本身的思考方式的有力的例子,明确表达了影响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我相信,我这本书所考察的小说作品,不是为了被供奉在任何文学名著的殿堂里而写的,而是为了赢得最广泛读者的信念并影响他们的行为。这些小说家根据他们的读者进行构思,希望人们用一种具体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汤姆金斯认为,应该把文学研究从所谓的名作扩大到通俗小说或流行小说,并承认这些小说的社会意义。因此她不仅赞扬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且还赞扬了《飘》这样的作品。她认为这样的作品谈到了宗教信仰、社会实践、经济和政治环境,虽不是那种将现实素材转变成艺术品的杰作,但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对广大读者的思想和行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大地》三部曲亦应属于研究的对象,因为它确曾在“改变人们思考和行为”方面发生过作用。为了说明这种作用,这里摘引几段关于《大地》的评论。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星期日纽约论坛》在书评部分写道:“一年前勃克夫人(即赛珍珠——编者注)的《东风·西风》出版时,我曾说那是第一部成功地用英文写中国的小说。现在,由于《大地》的出版,她可以算做第一流的小说家了……这就是中国,以前从未有人在小说里描写中国。不过,《大地》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任何一个地方人与土地的根本斗争,这种斗争在中国之所以更严重更富戏剧性,完全是因为那里的人单凭意志而斗争,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援助……”
埃德加·斯诺夫人曾回忆说:“一九三二年我初到中国时,《大地》刚刚出版。我吃惊地发现年轻的知识分子多么恨它……他们说:‘她不应该写那 些令人讨厌的人;她为什么不写富人、那些有教养的人呢?’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恨它,—因为他们不想让外国人知道任何关于中国不愉快的事馈;他们想隐瞒事实真相。我起初不理解这种观点。但后来我了解到那是因为他们当中一些人依赖外国人,依赖在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的西方人,或者受他们的保护,或者拿他们的薪水。他们想让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有个好的印象。赛珍珠认识到这点,她在写《大地》时,实际上是要戳穿这种谎言,揭露他们为了政治原因—面掩益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电影明星威尔·罗杰斯访问中国后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不消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会读书就一定该过赛珍珠写中国的杰作《大地》。它不仅是写一个从未写过的民族的伟大作品,而且是我们这代人所写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中国,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说这部作品是真实的,很少有作品写另一个民族而又被他们说写得好的……读读这本书,它会使你们不再胡闹,使你们了解到中国的一切。”
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语堂一家到达美国,在好莱坞看了MGM公司拍摄的影片《大地》以后,“林语堂宣称非常之好”。影片一九三七年二月公演后获得巨大成功,阿兰的扮演者为此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地》出版以后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正因为如此,“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因其杰出的传记作品”,一九三八年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当时,在广大西方人眼里,尤其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个既有悠久文化历史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他们想了解中国,对中国充满兴趣,赛珍珠的作品风靡一时,这完全可以理解。今天,美国人每年成千上万地到中国旅游,同样也想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想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的现在。他们听到中国的种种情况也包括着《大地》里的描写。他们今天阅读《大地》,亲身到中国去,都含有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目的。而在这种意义上说,《大地》仍然起着沟通两国文化的作用,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美国文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东方文化,固然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然而谁又能断然说《大地》没有起一点作用呢?也许他本人没有读这部作品,但同他谈论中国的人未必没有受过《大地》的影响。
最近,看过电影《一道长城》(A Creat wall)的美国人纷纷对这个表现中美文化差异的故事表示赞赏,这既说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说明了他们对两国文化交流的愿望。我现在对《大地》三部曲的看法,也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思考,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对它进行评价。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什么是文学和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的观念问题。我主张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拓宽文学研究的对象,正确看待古今中外的通俗文学。
对赛珍珠本人的评价,我想也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赛珍珠最初到中国来,是因为她出生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后来她在中国教书,是作为教会派出的教员。因此她在中国既是一种思想文化侵略的工具,又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文化知识。在外国人中间,她是比较接近基层大众的一位,目睹中国的现状,她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接受着一些影响。她在许多地方发表过同情中国的看法。她说,“我已经学会了热爱那里的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就决定为他们讲话……”她赞扬过蒋介石,但对国民党政府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她在哥本哈根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她关于中国的前途时,“她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和平的唯一希望,但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由于她的言论在报纸上广泛登载,中国国民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奖的授奖仪式。
赛珍珠曾经是斯诺夫妇的朋友;与林语堂先生合作写过剧本;她的好友萨拉·伯尔登还证实她与徐志摩在二十年代有过一段不明确的“爱情”关系,她的的《北京来信》许多地方是她与徐志摩关系的写照。她接触过中国的农民,也接触过国民党的要员,因此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必然充满种种矛盾。从人道主义出发,她对中国农民有同情心;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政策表示不满。但她的资产阶级本质决定她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她接受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宣传,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和恐惧。然而,她自幼生长在中国,后来又长期在中国生活,因而又对中国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不可能不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当人道主义占上风时,她的作品可能写得好些;而当她的反共心理占上风时,她可能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进行歪曲。应该说,她早期的作品较有人情味,而后期关于中国的作品大多数不够真实,有些进行了恶意的歪曲。
赛珍珠的极端反共开始于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她的这种变化,也应该历史地加以分析。一九四四年,美国国务院曾派出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塞尔维斯、雷蒙德·鲁登和约翰·爱默生等四位年轻的外交官到解放区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延安的工作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建议美国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后来赫尔利被派到中国谈判,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统一中国,而四名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年轻外交官则提出以毛泽东为首。结果赫尔利指责他仍受了共产主义赤化,使他们被迫解除了职务。紧接着就开始了麦卡锡主义时期。赛珍珠最初认为:“美国支持台湾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中国大陆不论是不是共产主义,仍是中国亿万人民的故乡;如果美国反对它只能使事情恶化。”但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图几家报纸同时登载的红色危险人物名单上列出了赛珍珠的名字,在这种形势下,她迅速以带刺的语气作了回答:“我不仅要否认现在和过去我对共产主义有过同情,而且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都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忠诚热情的美国人,我要说,现在一些美国人所进行的这种活动正在使我们国家成为全世界嘲笑的对象。其他国家的人民会感到惊奇。由于现在这种愚蠢的、大规模的、对上层和下层个人的随意指责,他们会问我们是不是个傻瓜的国家。我希望这种错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因而会使头脑清醒的美国人起来把它制止。”这里既反映了她的反共立场,同时也反映了她对麦卡锡主义的不满。
但麦卡锡主义并未立即停止。随着东西方阵营的形成和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赛珍珠的反共立场和对新中国的敌视日益明显,而且在有些言论中公开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歪曲,对中国的领导人进行攻击。这里既有政治形势的逼迫,两国互相敌对造成的误解,同时也有赛珍珠自己资产阶级的本质问题。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赛珍珠又表现出对中国的热情,自幼在中国长大的感情偏爱又萌发出来。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宣布访华以后,她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待中国”,积极准备到中国访问。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从未见过毛泽东,但我认识周恩来。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最近曾给他写信,期待五月间对他访问。”她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签证,几乎做好了一切访华的准备。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申请不可能获准。她受到很大的刺激和打击。不久她得了病,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逝世。她一八九二年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希尔斯保罗,幼年长在中国,后来在科特西·兰道夫——莫肯女子学院完成大学教育,此后又到中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尼克松在她死后的悼词中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从赛珍珠的一生看,她的思想前后并不一致,因此研究她的美国传记作家诺拉·斯特林称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女人。当她写《大地》三部曲时,应该说人道主义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因此作品总的基调比较真实;而那些不真实的地方,主要还是出于对生活了解不够和认识上的偏颇。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部作品并不是毫无价值,我们无须因她后来反共而彻底否定。她仍然因这部作品而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这部作品是被翻译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已经有六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会发展变化,而且一切变化都由多种因素决定。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不论政治观点和写作风格,发生某些变化乃至实质性的变化并不奇怪。有的会由坏变好,也有的会由好变坏,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因此应该历史地对待这种变化。我自己认为,西方新历史主义有些观点很值得借鉴,对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也可以用新历史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这样,通过把文学研究扩大到通俗文学和流行作品,对它们的价值进行新的评价,不仅有助于缩小文学研究与广大读者的距离,而且也可以避免对流行作品的笼统否定。
【注】该文为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中译本(漓江出版社,1989年)的《译本前言》。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相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