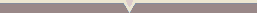大体而言,我把新中国50年的赛珍珠研究分作两个阶段,即五六十年代为第一阶段,八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数十年,东西方上直处于“冷战”状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长期处于政治上的对峙之中。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岐见,造成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阻隔乃至断裂。不夸张地说,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始终同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相伴随。就赛珍珠与新中国的关系而言,1949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一切已经今非昔比。而且自此以后,她(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再度沉浮。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外国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新中国的赛珍珠研究,也是始于1950年的一篇苏联人N·谢尔盖耶娃写的文章,该文原载苏联《新时代》第11期,后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北京《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4期上。该文对我国的赛珍珠研究向“左”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该文主要是针对赛珍珠的小说《亲族》(Kinfolk)来加以评论的。文章认为,“赛珍珠的书总是有一种巨大的缺陷,这就是她企图抹煞正在现代中国发生着的、巨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变迁。”其实,这个立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无论其处女作《东风·西风》,还是其代表作《大地》,都深刻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变革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谢尔盖耶娃对赛珍珠的主要指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赛珍珠对中国现实的表现是“非常片面的”,“她想把阶段斗争和中国的政治生活从读者视线中掩盖起来”。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应该把现代所发生的一切都囊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呢?我想,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赛珍珠忽视了中国人的“政治的要求和政治生活”,“她不了解也不愿了解这国家中正发生着的深刻过程的本质。她不想提到人民革命的发展。她不愿意正视在中国即将发生的事件”。据此,谢尔盖耶娃得出了吓人的结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战争里,赛珍珠并不是站在他们的一边的。”其实,这已经不是文学评论所应得出的结论了。对此,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第三,对《亲族》,谢尔盖耶娃认为,该书“描写了带有世界主义思想、被美国主义的毒素所娇养、腐蚀和毒害而忘记了祖国语言的青年人精神上的空虚”。如果真是这样,应该说,赛珍珠的作品也是有意义的。但谢尔盖耶娃仿佛忘记了自己的立论,得出了完全矛盾的观点。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其自相矛盾之处随处可见。比如,小说写了两代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梁教授移居美国,依旧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被喻为是高雅的美学家。而其儿女则不甘心这种远离祖国的局面,他们要投身到自己的国家之中,贡献自己的精力和学识。对梁教授,谢尔盖耶娃斥之为“反动入骨的”、“彻头彻尾的伪君子”。那么,相应地,对梁教授的儿女应该得出相反的结论才是。有趣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梁教授的儿女詹美和玛丽回到了祖国,并且留下来。他们设立了医院,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教大人们最基本的卫生常识。他们还在这里娶妻、嫁人,扎下了根。应该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举动了。但谢尔盖耶娃对他们的言行却不相信,并且“被整个情节的虚假所激怒”,她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无非是一些“由纽约回来的中国人矫揉造作的‘在人民中间巡礼’”、“装备着祈祷书和伤寒疫苗的美国传教士的最新翻版”的人物而已。文章通篇的用词也是极其吓人的,“无耻的诽谤”、“关于中国民主进步力量的阴险的、完全不合理的论断”、“虚伪滑稽”、“恶意而愚蠢的诽谤”等等完全脱离了文学评论范畴的语词。据此,作者将赛珍珠痛斥为“把自己的笔出卖给帝国主义压迫者”。这种分析和逻辑推理,是很难服人的。然而,谢尔盖耶娃的文章,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中国对在三四十年代曾给予赛珍珠的正确的——至少是正常的——评论,开始加以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谢尔盖耶娃的说法,“赛珍珠是透过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眼镜来看中国的”,为十年后的批判赛珍珠的文章定下了调子。
谢尔盖耶娃的文章发表后,在几乎十年的时间里,国内的赛珍珠研究无声无息。然而,在1960年,却同时有三篇文章问世。它们是载于《文学评论》1960年5期上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以及同时刊载在《世界文学》1960年9期上的两篇文章:《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析》和《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用不着详述这些文章了,因为它们在思路和批评手法上,乃至在用词和语句上,都与谢尔盖耶娃的文章如出一辙。
如果总结这个时期的特点,那就是,对赛珍珠作了全面、彻底的否定。就五六十年代的情形而言,我以为,赛珍珠被中国学者大加挞伐,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她不再居住在中国,而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时空完全将她阻隔到了中国之外。赛珍珠是1935年回到美国的。自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再也没有回到过令她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中国从此在她的眼里成了一个梦,一个幻影。在她眼里,中国再也不像从前那般玲珑剔透、清晰可鉴了,她对中国的认知似乎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第二,在她回到美国的最初几年,为了融入美国社会,她曾试图改变自己的写作主题,努力扩大自己的写作范围,把笔触伸向了美国社会。然而,这种尝试看来是不大成功的。作为熟知中国、又以写作中国题材闻名于世的作家,赛珍珠无法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于是,她很快又开始写作关于中国的题材了。在1949年后,她创作了《亲族》(1949)、《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1954)、《北京来信》(Letter frorn Peking,1957)以及许许多多的短篇小说、散文等。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她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很难说是全面和完整的。这当然妨碍了她对新中国情况的整体判断与理性分析。
第三,我们知道,赛珍珠对国民党是极其不满的。她在作品中对国民党的抨击是毫不留情面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赛珍珠对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是有所不理解乃至有些误解的。我在读她的作品时,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赛珍珠深知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变动,但在她的主人公要对革命做出评价、也应该做出评价时,她所竭力使用的是一些相对中性的词汇、甚至是闪烁不定的语句,而很少用偏向一方的价值判断。对此,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两点解释:一,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她对革命的双方也有她个人的看法,因此她不愿介人其中;二,作为一名作家,赛珍珠注重的是革命给大众带来的变革,而不是革命本身。这是由她的创作思想亠一要为普通的劳动大众写作——所决定的。当然,在她回到美国以后,她在一些访谈与散文中,倒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这原本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外国人和我们保持高度的一致,但在非正常的年代,这一切都被非正常地加以处理和批判了。
第四,赛珍珠对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误解,同样也被中国大陆的批评家所不理解和误解。赛珍珠的一些过激言谈和在作品中的敏感体现从大洋彼岸传至国内,立即遭到了国内学术界异常激烈的反击与驳斥。因此,赛珍珠迅疾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靶子之一。对她的评论也开始用政治标准取代文学标准,这样,对她的评论就走向了极端。
我以为,尽管这一时期的评论文章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但这并不说明它们毫无意义可言。
首先,历史地看,60年代的批评,既受当时特定历史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也与30年代的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不过60年代的赛珍珠研究更加走向了极端而已。实际上,在30年代的文章中,对赛珍珠的创作与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关系的批评已经初露端倪。如:胡风的文章,在指出赛珍珠的创作的缺陷时,就明白无误地谈到,“吸干了中国农村血液的帝国主义,在这里(指《大地》)也完全没有影子。”当然,胡风的意思是,赛珍珠没有将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写进她的代表作里。祝秀侠的文章,应该属于胡风文章观点的进一步延伸。她对赛珍珠的《大地》的定位是,“一本写给高等白种人绅士太太们看的杰作"。文章指出,《大地》“通过用力地展露中国民众的丑脸谱,来迎合白种人的骄傲的兴趣”,其目的在于,“惟有这样,才可以请高等文化的白种人来教化改良,才可以让帝国主义站在枪尖上对付落后的农业国家,才可以让资本主义来‘繁华’一下”,“且更巧妙地掩饰地为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行为张目”。作者的结论是,赛珍珠正是“站在统治者的代言人方面来麻醉中国大众,巧妙地来抹煞帝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的事实!”我注意到,祝秀侠在文章的至少18处地方都加了着重号(我这里所引用的都在其列),使用了至少8个惊叹号。可见作者在写作时所怀有的态度和激动的情绪。因此,我以为,在看待五六十代的批评时,不能忽视它与三四十年代的密切关系。将五六十年代的批评,仅仅归咎于时代的产物或是孤立地加以看待,就很难说具有一种真正的自省意识,也很难得出公正的结论。
其次,我想指出的是,即便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以上述三篇文章为代表的“政治批评”,也并非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遭受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与欺凌,这使得我国的学者与读者对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相当看重与在乎的。这样的民族情感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也是值得尊重的。这其中蕴涵着民族自尊心、阶级感情、特殊的历史背景、迥异的文化语境等问题。在赛珍珠研究领域里,赛珍珠是否具有殖民主义的思想意识?其创作思想是否表露了或是隐含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图?我想,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赛珍珠的创作与“殖民主义”、“帝围主义”的问题,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应当会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一直以为,“冷战”时期的文章,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与“文化”和“侵略”的问题,在后现代的今天,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论,但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60年代,赛珍珠研究是片空白。70年代,赛珍珠研究依旧是一片空白。
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大,赛珍珠这个被喻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人桥”的作家,重新引起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有这样一些大事,是应该被记入中国赛珍珠研究历史的:
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小说集《生命与爱》(林俊德译),其中收录了赛珍珠的三个短篇小说《少女之恋》、《生命与爱》和《报复》。这是赛珍珠作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首次亮相。
198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三步曲》(王逢振等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首次出版赛珍珠的巨著,其意义是重大的。该书受到了读者极大的欢迎。
1991年1月,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了“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重新评价了赛珍珠的作品及其创作思想,肯定了赛珍珠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1991年1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赛珍珠的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即《我的几个世界》,尚营林等译)199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赛珍珠评论家保罗·多伊尔所著赛珍珠的评传《赛珍珠》(Pearl S·Buck,张晓胜等译)。1992年,镇江学者刘龙先生主编了《赛珍珠研究》一书,其中“录有1991年1月在镇江市召开的************次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资料及国内新闻界广泛报道。”
1992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上海召开了“纪念赛珍珠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1992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开设了由郭英剑主持的“赛珍珠研究专栏,”几年来,其所发论文有三分之二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所转载。江苏《镇江师专学报》(社科版)也开辟了“赛珍珠研究专栏”,专发赛珍珠的有关评论文章。几年来,两份学报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挤出一定的“地盘”,致力于赛珍珠研究,成为国内赛珍珠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园地,为我国新时期的赛珍珠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述两次研讨会的召开、三本书的出版以及“赛珍珠研究专栏”的开办,对我国的赛珍珠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赛珍珠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研究成果之多,探索之深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以及五六十年代的总和。
1997年7月,南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一燕京学社在南京召开了“中美文化交流:184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中美文化交流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中,赛珍珠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我手头目前保留的资料来看 ,在当时书面提交大会的32篇论文中,有11篇是专门论述赛珍珠的,占大会发言总数的三分之一。
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大学刘海平、王守仁、张子清三位先生主编的“赛珍珠作品集”,出版了《大地三步曲》、《东风·西风》、《龙子》、《同胞》、《群芳亭》等作品,还几乎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步,翻译出版了美国赛珍珠研究专家彼德·康教授撰写的《赛珍珠传》(Pearl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这是一部“新的、从文化层面切入的大型传记”。
1999年4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郭英剑编的《赛珍珠评论集》。该书首次将我国近70年来的赛珍珠研究方面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加以搜集和整理。它是对20世纪中国赛珍珠研究的一个总结,使读者可以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现状。
我以为,八九十代的赛珍珠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较之60年代,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二,在深度、广度、高度上较之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两个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来。
第一,与60年代的极左倾向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内对赛珍珠认识的全盘否定的倾向,并且把赛珍珠研究重新拉回到了正常的文学评论的轨道上来。一些重新编写的辞典、辞书与教科书,开始改变对赛珍珠的评论态度,试图持一种客观评价的尺度。应该说,这是八九十年代赛珍珠研究所取得的一个极为明显的成就。另外,赛珍珠也成为许多高校外文系与中文系研究生的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之一。
第二,与三四十年代相比,这个阶段的研究已经趋向深入。人们在开始“拂去历史的尘埃”,历史地看待赛珍珠的同时,研究在逐步地深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一、赛珍珠文学现象的成因。有研究者从“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作为她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对妇女、儿童有特殊的眷恋,并作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对象”、“同情受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并在文学创作乃至社会活动中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尊崇中国文化,并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中西文化的交流”等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赛珍珠文学现象的成因。二、赛珍珠的文艺观。有学者认为,赛珍珠的文学理论有两个,一为“自然说”,也就是说,文学要顺其自然,不矫揉造作;一为“文学要有人民性”,即文学创作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民,为了更多的读者。三、赛珍珠作品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带来的启迪。有学者认为,赛珍珠的创作表明,“各国最广大的读者,对一个民族独具风貌的斗争史、心态史与反映这个民族富有个性的‘脸’的民风民俗,有着更多的‘共同兴趣’。它应是文学‘世界可比性’的‘定位点’。”赛珍珠作品中的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及她的立足生活,应该为广大的中国作家带来某种启示。四、纠正了以前赛珍珠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的史实。如,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将最先发表文章批评赛珍珠的学者康永熙(Yanghill Kang),误认为是中国人。从发现的新资料来看,研究者纠正了这个错误,事实上,康永熙是位旅居美国的朝鲜人。再如,有学者对赛珍珠中文名字的一些传闻、模糊认识乃至误解做了澄清。
第三,开始运用更多当代新颖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赛珍珠进行研究,使赛珍珠研究在理论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有:一、运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解读赛珍珠。这方面最早的文章,是从“西方女权评论家为何排斥赛珍珠”来谈起的。研究者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一向以女性文学成就为自豪的女权评论家,对多产作家赛珍珠及其作品视而不见呢?”从研究中,学者认为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赛珍珠的作品被认为已经过时;其次,赛珍珠的作品被认为不能充分反映女性文学传统;再次,赛珍珠的作品的中国题材难以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运用女权主义方法进一步深人探讨的文章,还有《一位需要重新认识的美国女作家——试论赛珍珠的女性主义特征》与《男权大厦里的怨恨者与反抗者》。前者对赛珍珠的著作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赛珍珠的观点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平行一致的。”后者认为, “赛珍珠无论在小说还是非小说中,都关注并思考着妇女的命运和地位问题,”进而对赛珍珠的诸多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进行了分析。二、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读赛珍珠。《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一文,依据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与《文化和帝国主义》(Cuitlre and Imperialism,1993)这两部著作中所展露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探讨了赛珍珠其人、其文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评价她。作者认为,赛珍珠应该被视为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先驱者。
第四,对赛珍珠的评论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一、在小说方面,不仅涉及到她著名的《大地三步曲》,更有过去不大被人提及的《母亲》、《东风·西风》、《牡丹》、《匿花》等。二、传记方面,赛珍珠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同时,为赛珍珠赢得极大声誉的、她为生身父母撰写的传记《放逐》和《奋斗的天使》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三、有众多的文章论述到了赛珍珠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赛珍珠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是东西文化的结合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不仅探讨了赛珍珠思想中的西方特色,更阐释了她作品中所展露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第五,同样注意到了对赛珍珠的作品进行微观分析。既有对赛珍珠作品人物进行文本分析的,又有对赛珍珠的作品细节的探讨。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当前的赛珍珠研究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她的作品正在逐步被译介过来,评论也在高度、深度与广度上现出特色。我相信,赛珍珠研究在21世纪会有更大的发展。
因为,赛珍珠研究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至今还是个需要也是可以进一步深人探索的课题。更因为,赛珍珠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