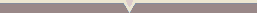卷一:遭遇巧克力的诱惑另一个赛珍珠(1)
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重译赛珍珠(PearlSBuck)的PavilionofWomen(据我所知,早在1948年,上海百新书店就出版过此书的节译本《深闺里》;前几年,漓江出版社推出过全译本,译名作《群芳亭》)的时候,正巧赶上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庭院中的女人》(美国银梦电影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上映。电影拍得好看——是那种故事完整、画面讲究、也多少说得出点意思来的好看,你应该让哪一个镜头点中笑穴,被哪一句台词逼出眼泪,都是事先拿捏好的。看这样的电影,你多半不会有怎样的惊喜,但也不至于惘然若失——我是说,假设你没有读过原著的话。
在此之前,我也一样没有读过赛珍珠。我对赛氏所有的印象加起来不会超过二十个硬邦邦的抽象名词:传教士的女儿,生于十九世纪末,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专写中国题材的小说家,诺贝尔及普利策双奖得主,传说中的徐志摩的情人……
有朋友听说我要译赛珍珠,劈头就问:“何苦来哉?”
他说得似乎有根有据:其一,赛氏得的那个诺贝尔,后人颇多争议,福克纳不是酸溜溜地说过“不屑与中国通赛女士共荣”吗?其二,她的小说几乎还是十九世纪的那种写法,其表现手法即便在当年也有落伍之嫌,现在重译有何必要?其三,评论界一般不会把PavilionofWomen列为赛珍珠最成功的作品(这一条我倒是不以为然,试想,如果凡非代表作皆不译不读,那我们的选择范围未免太狭窄了些;更何况,所谓“代表作”,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看看电影,你就该知道这不过又是一个传教士的爱情故事罢了,难道比得上《红字》、《荆棘鸟》?
在几乎要放弃之前,我到底还是先坐下来静静地把书读完了。说实话,我相当惊讶。我读到的,是一部完全不同于电影的小说,无论是情节,还是其核心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从小说里,我读到的是另一个赛珍珠。我当然不敢说电影的改编一定是败笔——如果从某种现代审美的角度来看,也许会有人说正相反。可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两者之间的不同。电影(尤其是后半部)里的诠释,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戏剧化的误读。而这样一部独特而诚恳的作品,是值得让看过或者没看过电影的人,有机会一窥作者原来的动机的。话说回来,虽然有这样的直觉,但是原著我只草草读了一遍,所以对于作者的用意——那种线条不那么明晰、形状不那么确定的东西——我仍然不敢说自己揣摩得有多么贴切。于是,探索主旨的兴趣紧跟在好奇心后面升起来。我想,应该没有一种方法,会比逐字逐句地翻译,更容易接近答案了。
另一方面,作品里大量描写中国风貌的文字,散发着一段我不甚熟稔却又不觉生分的时代的气韵,对于我,始终是一种诱引。给现在的中国人看美国人用英语写大半个世纪前中国人的故事,该用怎样的中文再现才最合宜呢?在那些写深宅大院、少爷小姐的细节里,能不能用上《红楼梦》的腔调(后来才发觉,以自己粗浅的双语功力,还远远没有到达这样的水准;至今想来,仍为当时的率尔操觚惴惴不已)呢?以前翻译总怕自己的文字里中国味太重,这一次“本土化”一把,好歹不会有什么不妥吧?
思来想去,我认定,这至少是一件有趣而有益的事。
从故事本身讲起。
小说里没有说明时间地点,但从细节上看,电影开篇中限定的“1938年,江苏的河边小镇”大抵是不错的。其实“山雨欲来”也未必“风满楼”,虽说远方的战火是早就烧起来了,可中国实在是太大,小镇里消息又不通达,顶多是略略瞥见两个火星子罢了。所以镇上大户吴家的头号实权人物吴太太(爱莲)还有心思琢磨一下给吴老爷纳妾的事。
彼时的中国,纳妾多少已经有些背时了。吴老爷虽然无用,却大致是个正派人;吴太太漂亮能干且贤惠,治家理财堪比王熙凤,博古通今不让薛宝钗,况且又替老爷生养了四个儿子。在外人看来,吴氏夫妇齐眉举案,吴家人丁兴旺,本没有再纳妾的必要。然而吴太太暗自拿定了主意,也不管吴老爷如何反对(实则半推半就),在自己四十岁生日那天昭告全家:从此不与老爷同住,还要火速替他娶个姨太太。
原来这惊人之举在吴太太心里蓄谋已久。自从十六岁那年嫁到吴家,爱莲就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服侍虚有其表而见识短浅的男人,谁都挑不出她的错来。现在她只是想把这副担子卸一卸,再不用为怀孕担惊受怕,替老爷鞠躬尽瘁。她要一头钻进故去的老太爷留下的书斋里,把那些“不该让女孩子看的书”读个够。
情节进展到这里,我们应该能读出一些味道来了:吴太太想要的是自由啊,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她说不上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缺憾,只是,这世上一定还有别的活法,她好歹得试一试。可吴太太到底不是娜拉,她要把一切都安排得四角俱全。她在传统妇道的范畴里找到了挡箭牌:纳妾之举既能让她全身而退,又能维持其一贯的贤良大度的形象,冠冕堂皇地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合府上下,虽心存疑窦,到底无可指摘。
吴太太选接班人的这一段写得煞是精彩:
那年轻女子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事儿吴太太琢磨了许久。此时,她又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毫无疑问,她得跟自己截然不同。她一定得年轻,可又不能比儿媳妇小,要不家里非乱套不可。二十二岁正合适。她的书不能念得太多,因为吴太太自己就挺有学问。她断断不能是那种摩登女子,一个女孩儿家,若是又摩登又年轻,哪会甘心当人家的姨娘,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把吴太太一脚踹开,整日整夜地勾住吴老爷的魂,那他们在这一大家子的儿孙面前还怎么做人?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爷们来说,纳一房妾还是一桩体面事,可他万万不能听凭她的摆布。她当然得有一副俏模样,可也不能漂亮到让宅子里的小伙子或者吴老爷自己找不着北。看上去顺眼、秀气也就够了。还有,吴太太自个儿的模样是这一种美,那闺女的模样就应该是那一种俏。换句话说,她应该是丰满红润的,骨架子大些倒没什么要紧。
赛珍珠能从这样的角度切入中国女子心里的微观世界,说实话,我初读之已称奇,再译之更是悚然——乃至肃然起敬了。
吴太太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耳根并没有就此清净下来:精挑细选来的二太太秋明犯倔,不愿曲意逢迎年纪大得可以做她爹的老爷,反而暗暗迷上了三少爷丰漠;吴老爷与秋明相看两生厌,吴太太又不愿再与他同房,干脆一头扎进了烟花巷;次子泽漠自由恋爱,娶了个新派的上海姑娘若兰,但是真的过起日子来了才发觉彼此的脾气、观念都不怎么对路,争吵不断;三子丰漠在母亲的“巧妙”安排下与会说洋文的漂亮小姐琳仪成亲,然而没过几天,后者骄横自私的本性便暴露无遗,家里给折腾得鸡犬不宁……吴太太发觉自己的如意算盘第一次落了空,既有的秩序第一次不那么管用了,暗流涌动中,她的信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卷一:遭遇巧克力的诱惑另一个赛珍珠(2)
此时,身为丰漠英文教师的传教士安德烈走进了吴太太的生活。此人强壮而睿智,眼光澄明,心底无私。他从未喋喋不休地布道讲经,而是身体力行地扶贫济弱、传播科学、倡扬仁爱,然言行殊为乖张,又非俗世可解。
吴太太却有知其异秉的慧根——照安德烈的说法,“她可真是个明白人啊”。他们交流、争论、探索灵魂,所有的读者都看得出来,似乎接下去唯一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双双堕入情网了。电影也正是这么拍的。虽然在此之前,小说中的很多细节在电影里已有了一番移花接木,但演到这里,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改编”。我们看到,大银幕上,一段“被禁止的爱”(forbiddenlove)在火光冲天、雷雨交加之夜终于跨过了灵肉之界,然后才是战争,是死亡(你是不是想到了斯佳丽和白瑞德?)一切都像这部电影广告中说得那样好莱坞化:深深庭院中,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如何演绎?纷飞战火下,两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怎样保全?
如果带着这样的印象和企图去看小说,大半会失望。因为根据原著的安排,浪漫故事还没来得及发生,安德烈就为了救人而死于青帮的歹人刀下。直到亲眼目睹安德烈的尸身,吴太太才恍然省悟,原来自己竟是爱着他的。
接下来,大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吴太太孤身一人在想象里反刍这份“灵魂之爱”,在尘世中实践安德烈毕生的信条、未竟的心愿。她收养了安德烈生前照料着的孤儿,支持留洋归来的丰漠到农村办学;她给秋明自由,也理解了若兰这样的“新式女子”,并用自己的经验解开她的困惑;她以宽容之心接纳了吴老爷的相好——粗俗的烟花女子茉莉;她以非凡的勇气为年过四十的“高危产妇”康太太接生,在大人孩子只能保全一个的情况下顶着别人的非议救了康太太一命。
所有这些觉悟与蜕变似乎都来自吴太太与安德烈之间“肌肤不亲、阴阳相隔”的爱情。赛珍珠没把它写成类似于“人鬼情未了”的传奇故事,而是强调那纯然是吴太太想象的作用。无论是竹影婆娑里的静谧,还是街头人群中的喧嚣,安德烈的幻象时不时地会从各种真实背景里浮出来,微笑着与吴太太对话——有的观点是他以前就说过的,有的则干脆是吴太太的揣测。这些经过她的头脑加工、提炼的信念逐渐构成了她全新的人生观。她的灵魂给整个儿提升起来,攀到了一个足以俯视庭院里的合家老小乃至整个世界的芸芸众生的高度。
小说末尾是渐渐老去的吴太太的一段心理独白:
当初她是如何打开门,让他进来的呢?她记不得了。有人把他领进来见她,于是她打开了自己的门,他就进来了,为她带来了永生。
是啊,现在她信了,有朝一日,即便肉身死去,灵魂仍将永存。她不崇拜上帝,也全无信仰可言,可她有爱,绵延不绝的爱。是爱唤醒了她沉睡的灵魂,让它生生不息。
她知道她将永生。
以下是最简略的赛珍珠生平流水帐,以及在我看来多少跟这本书扯得上关系的片段:
赛氏1892年生于美国,三个月大的时候就给身为传教士的父亲赛兆祥和母亲凯丽带到了中国。她从小生活在双语环境中,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水浒传》(后来大受好评的该书的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出自她的手笔)、《红楼梦》都对她影响深远。整个童年时代她一直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父母的狭小而洁净的长老会式美国世界和不那么整洁却充满欢爱的中国大世界。”她后来写道,“两个世界之间没有交流。”她本人究竟属于哪一个世界,是她一生都没能弄清的问题。
她的前半生,除了在美国短暂的求学经历外,大半都在中国度过。其间,她的足迹遍及江南各地,亲眼见证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二三十年代的内战。对于中国文化的神髓、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农村)的窘迫和悲哀,她感同身受。从念书时开始,她就积极撰文向美国人讲述她在中国的真实经历。所有不顾常识、胡编乱造的“中国见闻”都会让她义愤填膺。原因是再简单不过了:对她来说,中国是几十年来每日里周遭的平常世界,不是一大堆发霉长蛆的陈腐概念。
她的第一部作品发表时已过而立之年,然而一生著述甚丰,所有成功的作品都与中国有关,其中包括《大地三部曲》、《龙种》、《东风•西风》。可以这么说,美国人(包括其他外国人)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赛珍珠的作品。
她的书曾创造出惊人的销售奇迹,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同样大受欢迎,深受普通民众的爱戴。一度,她的运气好得惊人,普利策奖折桂之后又拿到了1938年的诺贝尔奖,获奖理由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
然而她从小到大尴尬的自我定位一直像阴影一样让她不安。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学者指责她的作品中关于贫困农村的描写“仅代表中国人生活中黑暗的方面”,而来自美国主流评论界的声音也不甚恭敬——赛氏的作品结构类似章回体,写法近乎白描,初读似略欠新意;她不擅长心理解剖,更不赶意识流的时髦,有时候未免显出一点说教的痕迹。何况,她是个女作家,题材和视角都有点“婆婆妈妈”,在当时男权话语盛行的美国文坛,怎么说都是异端。被排斥感始终让她对自己的写作缺乏自信,即便是拿到了诺贝尔奖以后。
她的个人生活值得提一笔:第一任丈夫布克也是个传教士,其不近人情、骨子里看轻妇女的个性同赛珍珠的父亲如出一辙。这两个男人给赛珍珠及其母亲带来的痛苦,在赛氏作品中有相当恳切的反应。在她的小说里,中国妇女所受到的压制往往具有普遍性,也是她本人的切肤之痛,是这世上所有的女性共同的悲哀。此外,她唯一的女儿先天性智力低下,这是另一桩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为了排遣忧伤,她一生收养了许多孤儿。
她乐于表达政治主张,却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到头来处处不讨好:她向来不支持共产主义,却也很早就预言“脱离中国农村”的国民党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在中国那段“没处讲理”的特殊时期里,她被国人视为“歪曲、中伤、诽谤中国人民”的作家,然而在美国,她又因为常常不合时宜地替中国说话而遭到联邦调查局长期跟踪;她从小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但又从父亲与丈夫身上看透了宗教里某些虚伪的成分,从来不在作品里掩饰讥讽鄙夷之情;她毕生以人道主义者自居,倡导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精神,同时又常常用中国人的儒家道家思想去解释问题……总之,她的思想是一锅内容丰富的杂烩,品尝者或赞或弹,多少都能咂摸出些许异味来。
1934年,赛珍珠在抗日战争前回到了美国。她觉得自己还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像以前一样。然而,历史另有安排。七○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她兴奋地像个孩子,多方奔走,要求到中国去。结局可想而知,签证申请被驳回。1973年,她在极度失望中辞世。在她自己设计的墓碑上,除了“赛珍珠”这三个汉字以外,并没有写下她的英文名字。
卷一:遭遇巧克力的诱惑另一个赛珍珠(3)
近年来,东西方对赛珍珠的价值都有重新评价的趋势。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赛氏曾受到的来自主流文坛的攻击是多么有失公允;在中国,她的小说译本终于出现在我们看得见的书架上。直到亲身阅读,我们才发现,相对于若干年前被妖魔化的那个“中国通赛女士”而言,我们通过作品感受到的,实在是另一个赛珍珠啊。
也许,只有知晓了写故事的人自己的故事,才更有可能接近故事本身的企图。
我有这样的感觉:赛珍珠独特的跨文化背景既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始终是横亘在她人生道路上的莫大的悲哀,让她的观念与主张永远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摇摆。
PavilionofWomen是赛氏一九四六年的作品,距她离开中国已有十多年时间。然而在大量关于中国人——不管是大富之家还是乡野村户——生活的细节,在她笔下依然真实鲜活,一如《大地》之类的早期作品。然而,就像大多数作家的后期作品往往会注入更多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一样,PavilionofWomen也在其主要人物身上负载了很多——应该说是太多——抽象的东西。就小说的美学价值而言,前半部出色的自然主义写法,或许要比后半部颇具冒险性的心理探索成功(至于像电影里那样公式化的浪漫处理,则更是连探索的诚意都没有了)。安德烈之于吴太太,与其说是理想情人,不如说是她后半生的盟友、导师。吴太太说,“我们用不着执手相看,就能融为一体。纵然肉身湮灭,此情依然能绵延不绝。我们并不是靠肉身才结合在一起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是很难理解如此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的。《赛珍珠传》的作者彼德•康德的说法或许能代表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困惑,“在一个吊人胃口的开头后,小说落入了一团玄妙的迷雾中。”
然而,也正是在这团迷雾里,赛珍珠努力打破东西方、传统与现代以及性别之间的差异,让主人公如凤凰涅一般地在思想交汇的洪流中完善自我,从而获得新生。或许,在赛珍珠看来,如此打磨锻造出来的思想才是真正客观的、人类应该追求的境界。安德烈的顿悟极富戏剧性,他原本生活在威尼斯,却在结婚前夕突然看破红尘,从此四海为家。他虽然皈依宗教,却只忠诚于心里的上帝,被教会视为异教徒;与安德烈相比,吴太太无疑更世俗化,更具有东方式的圆融通达——这也就注定了她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出格。哪怕是到了最后日臻默契的阶段,他们仍有不少观点相左之处。比如广义的宽容、忍让之道与追求个人幸福之间的矛盾,灵与肉之间的冲突,男女之间的鸿沟,等等。在读者看来,吴太太的思索时时闪烁着比安德烈更直接、更人性化的光彩,比如:
男人本身不也是女人创造的吗?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她,反而怨恨他,暗地里与她较量,主宰她,压迫她,把她锁在屋里,裹她的脚,束她的腰,不准给她报酬,不许她有一技之长,不准她知书达理,他一咽气就让她守寡,有时候干脆把她活活烧得灰飞烟灭,还胡说什么她是为了守节。
于是,我们看到,自始至终,吴太太,或者说赛珍珠本人都没有完完全全地被安德烈教化,也没有把自己说服。安德烈死后她的许多无私高尚之举,或多或少地有脱离实际之嫌。正像评论家们普遍指出的那样,赛氏的特长在于讲故事,但是在本书中,心理刻画的比重也许超过了她能熟练驾驭的范畴,有时候不免局促起来——她愈是试图为自己的思想理出一条不偏不倚、东西兼顾、高瞻远瞩的头绪来,那些矛盾的观点就愈是冲撞得厉害,煎熬着旋涡里的人物,也折磨着思悟中的作者。
然而有趣的、动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一个真实的、痛苦的、不知所措的赛珍珠在书页间辗转反侧,上下求索。读着读着,便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我们没有她那样的经历,永远不可能站在她的立场上“东张西望”,但是她的作品,却树起了一面角度诡异的双面镜,让我们照见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转过来,又瞻望到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可能性。
这样的角度,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作品,哪怕再不完美,也是值得记忆的。
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五味杂陈。我经常惶惑于自己辞藻的贫乏——横在我面前的是两座植被截然不同的语词的密林,好容易从一处突围出来,又陷进另一个迷阵难以脱身。最后的成品,是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努力保持平衡的结果——惟其刻意,不免处处露出斧凿之痕,明眼人略掂掂分量,大抵就能看出它底气不足的毛病来。
关于书名的译法:亦步亦趋,自然应作“女人的庭院”。最终定为《庭院中的女人》,固然有“同名电影热映在前,不妨顺势跟进”的商业考虑,也因为小说的重心始终落在“女人”而非“庭院”上——吴太太做梦都想从这四方庭院里飞出去,看看屋外的天空;末了,她的思想摆脱了肉身的羁绊,翱翔于寰宇间。于是她知道,她将会永生。
附:作者简介
黄昱宁,一九七五年生于上海。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播专业。现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发表译著近百万字,其中包括小说《庭院中的女人》、《撞上门的女人》和传记《狂恋大提琴》等。杂文、随笔刊于《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