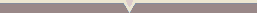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王守仁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名字是与《大地》联在一起的。不少人以为,赛珍珠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仅仅是因为她创作了《大地》三部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此殊荣授予赛珍珠,理由是“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多彩和史诗般的描述,以及在传记方面的杰作”。赛珍珠的传记“杰作”是《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其传主分别是她的母亲凯丽和父亲安德鲁(中文姓名赛兆祥)。赛珍珠自小跟凯丽和安德鲁住在中国,他们对女儿的生活、创作和思想起过重大影响。
“传记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传记这一体裁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又有一定的文学性。传记的对象是特定的某一个具体人物,即传主。传记必须遵循一切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没有创造事实的自由。但是,传记并不满足于生平事实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要展现传主性格的真实。为了揭示传主的精神世界和性格动因,传记作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可以加以合理猜测和补充。传记需要客观,然而,绝对的客观性只是一个幻觉。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一种文本。历史学家再现客观事实的过程同时也是阐述主观认识的过程。因此,传记是传记作者建构的文本,受特定历史条件、时代、读者等因素制约。赛珍珠根据儿时的回忆、平时的交谈、亲朋好友的叙述、实地访察和合理想像,撰写《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讲述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生活的故事。赛珍珠对传记材料的选择、处理和解释,传达了她的思想认识,反映出她的主体精神 《异邦客》实际上是赛珍珠写的第一部书。1921年10月,她母亲在中国镇江因病去世。赛珍珠在她的个人传记《我的几个世界》中回忆道:“当我办完丧事回到南京我的新家后,我迫切希望能使母亲复活,于是我开始为她写点东西。我当时想这是为我自己的孩子而写的,他们可能因此对我母亲有个印象和了解。”1926—1927年间,赛珍珠在南京的住所遭到军队士兵洗劫,但《异邦客》的书稿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没有丢失。据赛珍珠称,她在1936年发表这部传记时,基本保持了原样,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都未作大的修改。
赛珍珠在《异邦客》的开头就告诉读者,她对往事作了一番筛选工作,从几十幅画面中选了最能代表她母亲凯丽的一幅:“她站在中国城市阴暗中心的美国式花园里”。花园里种的是美国花卉,砌的是英国紫罗兰花坛;花园墙外是中国城市肮脏的街道、瞎眼的乞丐、挤做一团的房屋。这一墙之隔,把两个世界截然分开: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异教,白人与黄种人,文明与落后。凯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辈子,在异国他乡努力营造一个美国式家庭。在《异邦客》中,赛珍珠描写了在中西文化排斥、冲突、交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感受。赛珍珠将笔触深入到凯丽内心深处,展示她宗教信仰的迷茫和萦绕心头的乡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凯丽并不是一个女传教士,而是一个饱受创伤和磨难的普通外国女人。
凯丽祖籍荷兰,她的祖父曾在乌得勒支经商。为追求宗教自由,他不惜放弃兴隆的生意,携全家移居美国。凯丽继承了家族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在少女时代就为灵魂得不到拯救而苦恼,焦躁不安地寻求上帝的征兆。她许下诺言,假如上帝对她表明他的存在,就当传教士。凯丽听到母亲临终前喘息着说:“嗨,这——全是——真的!”以为这句话就是上帝的征兆,便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凯丽后来遇上安德鲁,他为了到中国去做传教士,正在寻找一位妻子,因为他母亲有一条规定,他必须成了亲才能去那个异教徒的国家。1880年7月8日,凯丽同安德鲁结了婚,婚后便启程前往中国。
凯丽为使自己的灵魂得救,为了上帝的事业,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前往陌生的国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一百多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经济落后,灾难深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不请自来”的外国人缺乏信任,没有好感,传教士的性命安全甚至也得不到保障。年轻的凯丽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来到中国,日子过得艰难。她生下七个小孩,其中有四个因病得不到医治,先后去世,给她刺激非常大。这些孩子如果是生活在医疗条件较先进的美国,是可以得救的。面对异国他乡的拥挤、肮脏、贫困和敌意,她日益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她后来回美国探亲,发现随着岁月的推迟,家乡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祖国变得陌生,把她忘了,不再需要她。在美国,“她也只是一个客人。在她自己的国家已不再有她的家,已不再有她的归属之地。”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痛感有国难回,最后打消了回美国的念头。凯丽的“无家可归”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她最初是为着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目的到中国来的。到达中国后,她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的落后状态感到吃惊。她难以理解仁慈的上帝竟然能容许人间有这么多的痛苦,内心里开始怀疑上帝的公正。她把自己奉献给神,并盼望被接受,但一直没有见到被接受的征兆,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在情感生活上,她丈夫未能把她视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安德鲁一心忙于传教,并不顾家。夫妻之间存在隔阂,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对安德鲁很反感,不要他到身边来。《异邦客》英文书名为(The Exile),也有“流放”的意思。凯丽作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是一个多层意义上的流放者:在宗教信仰上,被上帝放逐;在生活上,被自己的祖国放逐;在家里,被丈夫放逐。所以有人把这本传记译为《流放》,也不无道理。
凯丽是位双重性格的女性。一方面,她是一个清教徒,“拼命追求上帝”,要“作更深的奉献”;另一方面,她“富于热情和感情”,热爱生活,喜欢唱歌作诗,跟孩子们在一起,她为自己未能与上帝交流沟通而内疚,把孩子的夭折看作是上帝对她的惩罚。“由于意识到宗教上的失败,就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的另一面——富于热情和感情的一面,她被教导这一面是邪恶的,是引导她背离上帝的。她的两个方面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凯丽“终生以最大的意志力压抑在自己心中的怀疑主义”。临死之际,她表现出对今世应该享受而又没有享受到的美好生活的自然向往:她欣赏着女护士的舞姿,感叹道,如果有来世,她要“选择生活中快乐明亮的东西,如跳舞,欢笑和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讨论传记写作时指出:“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如果我们想到真实是某种如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是某种如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再想到传记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融合成浑然一体,我们承认这是个棘手的题。”赛珍珠在《异邦客》中较为成功地展现了她母亲“复杂的性格”,塑造出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凯丽不是女圣徒,而是一个活生生、“富于人性的人”。
异邦客》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常常进入母亲的内心,用她的眼光来看世界。由于历史的原因,凯丽“有一定的种族偏见”。她不喜欢附近寺庙阴沉的钟声,讨厌中国古老帝国的红色和黄色。在她眼里,美国是个“洁净、美和正直”的国家,中国则“缺两样东西:洁净和正直”。凯丽初抵中国,乘坐平底帆船从上海去杭州,岸上有许多人观望。“他们看起来多么可怕、小眼睛多么残忍、好奇心多么冷酷。”这是凯丽当时的感受。赛珍珠随后笔锋一转,跳出人物视角,评述凯丽对居住在运河两岸中国农民的认识:“她看出他们是家庭成员而且是靠土地养活自己的人,对她来说他们是人类,而且此后永远不再是‘异教徒’。这是后来她在他们中间生活的基调。”赛珍珠在《异邦客》中通过不少事例说明凯丽在同普通中国人的交往中逐渐克服偏见,称赞母亲怀有一颗“温暖的人类同情心”。凯丽具有模仿天才,很快学会了中国话。她作为一个女人,与中国的母亲、妻子平等交谈,“凯丽学会爱这些女人,很轻易地便忘记了她们之间民族和背景的差异”。凯丽最初出于宗教的热忱离开了美国。在中国生活多年后,她渐渐地意识到,虽然就出生和爱而言,她的根在美国,但是她也与中国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有另一些同样深的根。她有她的朋友,那些中国妇女”。凯丽最后决定留在中国,并不是为了继续寻找上帝,而是因为“那些不快乐、不幸的、受生活压迫的人们的召唤”。在这片土地上,她没能找到上帝的征兆,却发现了中国的“可爱”和人民的“和善”。凯丽晚年时,中国“对于她已不再是异国”。赛珍珠在回忆母亲与中国的关系时曾说过:“她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人民融合在一起了。”
凯丽是赛珍珠的母亲,也是她的老师。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凯丽在家里教育女儿,为她遂美国大学作准各。赛珍珠的英文写作得益于母亲的严格训练,这一点她在《自传随笔》中说得很清楚:“从我孩提时代起,她就教我写下我所看到和感到的事物,并帮助我去领悟到处存在的美。每周我都要写些作文让她批改,她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很体贴。”在《异邦客》中,赛珍珠提到凯丽喜爱小说,因为她内心深处总是充满人性。在母亲的熏陶下,孩子们从小就开始阅读狄更斯的小说,培养了对优秀作品的鉴赏力。赛珍珠对此充满感激之情。
《异邦客》是赛珍珠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创作的,作者没有摆脱哀思,十分伤感。其中对父亲安德鲁提得很少,态度显得很冷淡,这显然是受母亲的影响。安德鲁在《战斗的天使》中得到了充分的谅解,整个传记洋溢着女儿对父亲纯真的崇敬。作为练笔之作,《异邦客》写作上基本按年代平铺直叙,缺少起伏。与《异邦客》相比,《战斗的天使》要成熟得多。这部传记成书时间较晚,也于1936年发表。诺贝尔奖委员会评委、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曾透露,她之所以投赛珍珠的票,就是因为《战斗的天使》写得出色在许多方面,《战斗的天使》与《异邦客》都不同。赛珍珠在《异邦客》中着重写她母亲的感受,展示了她的情感世界。《战斗的天使》的副标题是《一个灵魂的写真》。在赛珍珠的笔下,一个只有灵没有肉的天使般圣者跃然纸上。这本传记的叙述结构尽管按时间的顺序直线进行,但作者常常暂时打断叙述的连贯性,插入一些议论,抒发自己的感想。
安德鲁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七人当中,有六个人当了牧师。安德鲁十六岁时,一个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到他家做客,提出要找一个人去中国。安德鲁对此起先充满恐惧,最后觉得这是上帝的召唤,便立志当一名传教士。他父亲要求儿子们在二十一岁之前必须在家帮他干活,然后可以自己出去闯荡。安德鲁不喜欢种田,一到二十一岁,他就骑马离开家乡去华盛顿一李大学念书。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不久进神学院深造,以取得做传教士的资格。他要去中国当传教士的计划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但得到母亲的支持,不过她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找个姑娘结婚,让妻子和他一同前往。安德鲁到哥哥的教堂帮助工作时,与凯丽结识,使他有机会实现去中国的这个目标。
安德鲁真诚地献身于宗教事业,以满腔的热忱从事他所热爱的工作,并从中得到乐趣。“打从前往中国那一刻起,就是五十年纯粹的幸福。”安德鲁在中国一直心情舒畅,这与凯丽截然不同。凯丽所追求但未能实现的与上帝的交流沟通,他能够做到。安德鲁为人正直,心地坦诚,全身心投入传教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上帝。他为事业、工作、信仰活着,长年在外奔波,忘掉了家庭和孩子。他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妻子,不会亲近孩子。赛珍珠儿时不喜欢父亲。后来,他年老体衰,需要女儿照顾,赛珍珠才“逐渐理解他,珍爱他”,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安德鲁是一个生活在梦里的人,一个着了魔似的人。对他来说,生活和人情无足轻重。他从未生活在尘世上”。他是“一个活着的灵魂”。安德鲁于1931年8月31日在中国庐山去世。赛珍珠在同年9月为他举行的追思礼拜会上,通过对安德鲁在华五十年传教生涯进行忆述,表达她对父亲的哀思、爱戴与缅怀之情。她说:“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去世了;一个急人所急,有求必应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赛珍珠塑造的安德鲁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在《战斗的天使》中,她常常对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例如,他为了能走水路传教,决定买一条船。传教团董事会后来写信,责令他解释为什么把用于建造教堂的一千美元用来造一条船。信上说:“希普利先生是我们最富有的捐献者之一,以任何形式得罪他都是不明智的。”读到这句话,安德鲁两眼闪过一丝寒光。难道就因为他是富人而必须服从他!富人要花大力气才能进天国,而他,安德鲁,竟要在上帝面前向他低头!他马上坐了下来,蔑视和气愤未消,写了一封他的孩子们称之为上帝全能的信,用简短、明确的话责问董事会为什么向玛门屈服;他们又何以配当上帝之工作的领导?至于他,他不会听从任何富人或他们之流,而只听从上帝。船造好了,他要用它。
结果,他再也没有接到富人或董事会有关这件事的任何信件。他“喻快地、满怀胜利地”使用那条船好多年。
安德鲁生活的时代是西方殖民主义向海外扩张的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对此,赛珍珠看得很清楚。她认为安德鲁和他那一代人并非温顺的眷恋桑梓之辈,也不是过惯恬淡生活的陆居之人。即或他们没有远走他乡充当果敢的传教士,那他们也会去淘金,去两极探险,或在海盗船里威临四方。如果不是上帝在他们年纪轻轻时就控制住他们的灵魂,那他们也会以另一种权力方式去统治异域的土著的。西方传教活动是在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世界建立起一个“神灵帝国”。安德鲁普世布道,“要世人知道他的上帝是唯一真正的上帝,万众必须向他致敬”,这表现出“精神上的帝国主义”。毛主席曾明确指出:美国人到中国来传教是一种“精神侵略”。就人品而言,安德鲁是一个“品格正直,目的高尚和好心好意”的人。他“虔诚地信奉上帝和圣命圣意”,确实是抱着拯救人类灵魂的理想,远涉重洋,到中国来的。安德鲁也算得上一个开明的传教士,对中国人充满同情。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信奉的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上帝”。安德鲁并没有意识到传教活动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部分,客观上是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服务。赛珍珠虽然出身传教士家庭,但从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她幼年时听中国老保姆讲故事如痴如醉,后来又跟家庭教师孔先生学习儒家经典。在长期中国文化的熏陶下,她已习惯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世界,从中国人的立场说话。小时候赛珍珠在寺庙里看到观音菩萨,联想起《圣经·旧约》里那个非常严厉的上帝。瞧着慈眉善目的观音,这个美国小女孩觉得自己更愿意同菩萨在一起,因为她喜欢观音脸上浮着的宽容仁爱、通情达理的表情。”赛珍珠在思想感情上与中国认同,使她对西方传教活动持批评态度。两部传记中,都不乏对传教士生活阴暗面的揭发。她对传教的必要性进行质疑:“为什么他们(信徒)要从自己的人中间走出来,去听这个外国人说教呢?为什么他们要舍弃本民族的安全稳妥,去相信他呢?”赛珍珠曾经说过,想起白人在远东干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她讨厌白人牧师在亚洲宣讲道德善行。如果说凯丽是身不由己地成为传教事业的牺牲品,安德鲁则是心甘情愿地为着一项错误的事业奋斗。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人都有悲剧性。赛珍珠的两部传记剖析了她父母的内心世界,写得深刻感人,被誉为“充满生命的佳作”。
本卷收录的《东风·西风》(1930)是赛珍珠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早在1925年,赛珍珠在《亚细亚》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一个中国妇女的谈话》。不久,她应美国一家出版商之约,又写了一个续篇。《东风·西风》分上下篇,便是根据这两个短篇改写的。小说采用独白式书信方式,叙述者是一个名叫“桂兰”的新婚妻子。“上篇”讲述桂兰自己的故事。她是老式中国人家的女儿,从小母亲就向她灌输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传统思想。她嫁了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丈夫。他坚持把妻子当成平等的人,逼着她把裹着的脚松开。桂兰为了取悦于丈夫,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女人”。“下篇”围绕桂兰哥哥的婚姻展开,在原有的新旧两种生活方式冲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异族通婚的矛盾。她哥哥到美国去读书,同他导师的女儿玛丽坠入爱河。他和玛丽在美国成了亲,然后与她一同返回中国。但是他父母坚决不认这个外国媳妇,她哥哥被迫与家里一刀两断,放弃家产,靠教书独立生活。小说以他们的儿子出生结尾。《东风·西风》虽然采用中国女子的叙述视角,但这部小说的语言是英语,是为美国读者写的小说。赛珍珠描述的夫妻和父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关系。桂兰来自封建落后的东方,而她丈夫“出过国,留过洋”,代表了开明自由、科学进步的西方。桂兰是在表现出愿意克服自己的愚昧之后才被丈夫接受。她哥哥从美国娶了个妻子回来,言谈举止都已完全西化,为家族所不容。但到最后,代表“陈腐事物”传统的母亲生病死去,而他们的“聪明”、“健壮”的儿子降临世界。东风和西风是朝对立方向吹的风。在赛珍珠这部作品里,处于强势的西风显然是压过了无力的东风。桂兰猜测,她哥哥的孩子将来“会理解两个世界”,“他会属于两个世界”。这个猜测实际上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愿望。
《东风·西风》出版的意义在于树立了赛珍珠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信心,为她创作《大地》积累了创作经验。她这时意识到,开发一个中国题材小说的市场是切实可行的。赛珍珠曾说过,明白这一点对她本人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那个阶段,只有中国是她唯一比较熟悉的创作题材。
王守仁
1997年10月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相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