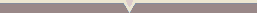作为一个很有理论建树的杰出作家,赛珍珠在其创作和论说中充溢着高明的辩证思想,而正是这种出色的辩证思想,使赛珍珠能具备观察和理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生活和中国人民的独特眼光。本文试就这个角度,简论赛珍珠的创作和论说的杰出贡献。
一、赛珍珠对自己认识中国的辩证认识
赛珍珠自幼生活在中国,热爱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她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已很深入。但赛珍珠本人,清醒而辩证地认识自己对中国的了解。1933年3月1 3日,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向西方阐释中国》演讲中坦陈:
我不是一个权威阐释者——当然也不是阐释中国的人。我向来就非常讨厌人家把我称为中国的阐释者。我是小说家,一个纯净而普通的小说家,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人,我都不负有任何使命,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有人问我“中国真是这样的吗?中国人讲这个吗?中国人是这样的吗?”的时候,我只能回答道:“我不知道,也许,中国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吧。我只是在那儿看到过。但是,他们是中国人纯属巧合;由于偶然的因素,我才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生活。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的心灵和行为,而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的心灵。
赛珍珠因对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而被邀请作此讲演,她在三个层次上对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发表自己的辩证认识。第一,她对于中国既知道又不知道,因为“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多样,风俗各异”,“我甚至都不敢说自己能够充分阐释亲眼目睹的人或事。我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以我小说家的方式来描写一些我认为是真实的人物”,也即她自知自己作为个人,不可能了解一个国家的全部,只能就自己的小说家角度了解和理解中国。即使是中国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如此辽阔、国情如此复杂多样的国度,普通百姓甚至连自己国家的事情都不甚了了”,这是因为“阐释者受到阅历的限制,不管其阅历多么丰富,那至多是一个人一生的阅历罢了。此外,限制他的还有其观察的视角,还有其特殊的使命感。”。第二,即使如此,“甚至都不敢说自己能够充分阐释亲眼目睹的人或事。”这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客观而辩证地作出自我评价。第三,自己生活在中国,并非主观的选择,并非对中国原存偏爱,而是命运的安排,因为父母在中国传教,带着她在中国常年生活,所以“由于偶然的因素,我才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生活。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的心灵和行为,而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的心灵。”她是从“人类的心灵和行为”来观察和描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的,从而不带任何偏爱和偏见。她进而指出:“问题是没有哪一个人的阐释是充分的,甚至一群人的阐释也一样达到准确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阐释汇集到一起,然后,努力寻出哪些观点是共同的,并讨论差异的意义所在。看到阐释不可能达到充分即完美的地步,强调群体认识的相同和差异同时存在,重视差异的意义,充分体现了赛珍珠思维方法中的辩证思想。赛珍珠曾说:“我在早年就认为,在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绝对真理,有的只是人们眼中的真理,真理也许是,事实上也就是个多变的万花筒。”。赛珍珠的上述观点富有辩证观念,而且这已成为赛珍珠自己的认识论的总纲,她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实践这个总纲,所以她的创作和论说中充溢着辩证思想,在这篇讲演的最后,赛珍珠更认为:
阐释者必须有一种谦卑的、调查研究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他就能抓住一切机会,对用释对象去刨根问底,同时,又能对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阐释能力不断提出质疑和挑战。
赛珍珠对于自己中国题材的创作和论说当然充满自信,她同时又注意保持谦卑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对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阐释能力不断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样的辩证态度,不仅使赛珍珠本人获益非浅,而且对所有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赛珍珠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辩证认识
赛珍珠的众多作品以中国和中国人为题材,诚如徐清博士所说:“赛珍珠笔下的人物就像是一直从远古走来的,他们生于土地,作于土地,死于土地,生命来去似有定时。赛珍珠以其天性的单纯诚挚,抓住了‘生’与‘死’这样基本得无可再基本的生命环节,以春夏秋冬这样现成而纯粹的自然现象为节奏形式写出了乡村生命圈永恒的生死循环。”赛珍珠实际上从这样的永恒的生死循环中写出了中国近现代民众的螺旋型的进步和变化,表现了她的辩证的时代观。
赛珍珠不仅在中国长期生活过,而且还曾经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生活过。《大地》便是描写中国最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的杰作。她对此类农民及其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朱刚先生曾正确指出赛珍珠在作品中表现出这样的看法: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 “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阿兰和梨花)表现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和发表《大地》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王龙、阿兰等人的性格,具有稳定、保守等特点,是儒家文化的体现。赛珍珠能正确地看到这种文化传统的优点和缺点,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五四运动后,儒家学说已被彻底否定,农民的逆来顺受即温顺的性能格、忍耐、漠然的品性,也被否定。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是革命,而农民的这种保守态度和性格,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赛珍珠本人也同情和赞同中国的革命,甚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表示过拥护。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她能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影响下的农民品性的优点的一面,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难以得到认同和赞赏,在意料之中,只有时过境迁,在70年后的今天,痛定思痛,才能看出赛珍珠目光和思路的真切、客观和可贵。根据赛珍珠发表此类小说和演讲的20世纪30年代的形势,中国的时代潮流无疑是革命。一部分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革命,参加了革命军队,最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理所应当地受到高度赞扬和歌颂。但事物还有另外一面,国统区的农民忍受剥削,种地交粮,没有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整个民族便无法生存,革命军队解放这些地区时,将面临一片荒芜、长期难以恢复原有生产水平的土地,和毫无生产资料、生活资源,静等救济的几亿农民,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如何维持和生存?建国后,中国建设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至今为止的全过程中,众所周知,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工人和其他阶层相比,农民贡献大而获得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大多起来造反,不事生产,甚至有不少人陷入派性和武斗而不能自拔。当十年动乱结束时,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农民,主要的是因其忍耐保守的性格,坚持种地生产,使全国人民还有饭吃。如果领导发生失误(如在“文革”中),群众如都马上起来造反,经济就要崩溃,此时便需要国民中温顺、忍耐的一面来做调节,缓和局面,让领导有吸取教训、调整政策的机会和时间,如果一味强调激烈斗争、阶级斗争,尤其是发动全民斗争,就会引起全国大乱,文革十年动乱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所以传统思想中的保守、忍耐的一面,也是历史的必需。试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农民年年造反,不事生产,固然彻底抛弃了忍耐、温顺的品性,坚决不让别人剥削,但国家和民族还能生存吗?更何况由于时代发展阶段的限制,造反起义成功,新政权维护的依旧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永无止息的造反,于事无补。因而对于传统文化和农民品性中的保守、忍耐,须持辩证的态度,而不能不看时代和形势,作绝对的全盘否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赛珍珠也并非一味强调农民尤其是妇女的温顺柔和与逆来顺受,她给歌颂造反的小说《水浒传》以极高评价。至于赛珍珠看到“美国流行小说和电影中的恶棍坏蛋全是狡猾的、心地阴暗的、来自东方国家的 ……而中国小说或电影里的恶棍则是身材高大的蓝眼睛高鼻带有卷曲的红毛,是英国身材、英国表情”,并发现“恶棍总是对方那个家伙”,这样绝对的看法,当然是片面而错误的,赛珍珠在自已的小说中则写出了中西各种人等的真实面貌。
赛珍珠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看法也颇有辩证观念。她在《我所知道的中国》、《我的中国世界》等文章中,非常推崇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考试制度能成功地选拔出最有思考力的人才,为科举制度服务的教育体制和科举考试制度具有公正和平等的优越性。但她同时也指出:“皇帝设想出一种用他们自己的知识来控制他们的方法,使官方考试成为在政界晋升的唯一途径;那些极其困难的考试,使人们为了准备考试而耗尽整个生命和思想,使他们忙于记忆和抄写过去的死的经典而无法顾及现时和现时的错误。对于众多才能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如此。赛珍珠无疑在基本肯定科举制度的同时,也看到执行这一制度的统治者在夹带私货时带来的弊病。正因具有辩证思想,所以她对科举制度的弊病的认识,是有分寸的,兼具历史和现实的卓识。对她所看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赛珍珠在自己的小说中,既描写并批判了部分人士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轻视和脱离民众,且又自私自利、软弱虚伪,诸如《同胞》中的自视极高、鄙视民众的梁博士、《上海景色》中不堪铁路小职员庸劣生活而发疯的大学毕业生源、《发妻》中留学回国后抛弃发妻害其自杀的李元、表面上做得好看实际上却非常不孝的留学生夫妇等等;也表现接近民众为民众服务的知识青年,如《同胞》中放弃国外优裕生活、回到故乡农村工作的梁博士的子女梁詹姆斯和梁玛丽、《群芳亭》中带领儿媳长住农村造福乡里的吴太太、她的两个媳妇露兰和琳琦、留学回国后跟着母亲在乡下办学的峰镆等等,还着力歌颂《东风•西风》中鼓励和督促妻子冲决封建罗网平等对待妻子的桂兰的丈夫。她并不将中国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模样,而是全面且又具体地观察并予以描写。
赛珍珠对中国现代民主的预言性评论也引人注目。她说:“等到中国现代民主得到发展的时候,它将是以自己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等同于美国式的民主,不过,在它自己的形式中,这一民主将提供给所有民族都渴望得到的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必不可少的机会。”正因为她掌握了高明的辩证思想,所以她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能作出正确的预见,更能以宽容的眼光肯定不同于美国式的中国民主。赛珍珠既认为“普天下人是一家”,又看到不同民族必有的差异性,不能强求一致,必须认识到“没有哪一个人的阐释是充分的,甚至一群人的阐释也一样。达到准确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阐释汇集到一起,然后,努力寻出哪些观点是共同的,并讨论差异的意义所在。”
三、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辩证认识
赛珍珠热爱中国古典小说,并从中学到了写作方法。作为一个美国人,她写的是地道的中国小说,著名出版家和评论家赵家璧先生认为:“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色。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赵家璧说“除厂叙写的工具以外”,指赛珍珠用的是英文,而非中文,但赛珍珠本人甚至认为“在描写中国人的时候,纯用中文来织成,那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故事,我不得不再把它们逐句译成英文。”。在赛珍珠的小说中,人物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在写作方祛上,她喜欢用中国小说常用的开门见山法,结尾则喜用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无收场的收场”,她认为这与西方小说“解决了一切”的结尾完全不同。她说:“在西洋,我们就喜欢去知道故事的收场,我们要知道谁与谁结婚,谁死了,每个人的结局都要知道,于是我们掩着书儿满意了,忘掉了,于是再去找第二本。因为着这小说既解决了一切,我们就无庸去再想。在中国人,就喜欢想下去。这也许是中国人所以把他们有名的小说,趣味无穷的念了再念到几百遍的理由了,他们像是常可以在那儿找到新东西的。我得说,假若一个人养成了这种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是味同嚼蜡了。”
热爱中国古典小说的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与一般西方人不同的见解。朱刚先生介绍赛珍珠于1932年在华北某校所做的两个报告《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 West and the Novel)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中的重要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连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进而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对于结构上如此“不严肃”的作品,赛珍珠仍坚持称为艺术品,她说: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指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不仅认为中国的古典小说(即“早期中国小说”)有其艺术形式,而且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她还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的以上观点,清楚地显示了她的辩证思维的优越性。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不同的是有头有尾,即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叙述方法是顺叙,没有跳跃性,思想的倾向性明确,而根据赛珍珠的转述,西方学者的看法竟然相反。“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一语并非说没有标准,而是说她并不持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所以赛珍珠能用辩证法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细分析中国小说“无形中的有形”,即在西方人所谓中国小说的没有形式中看到特殊的形式。中国古代文论家有“至法无法”的理论,我认为在“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一语中,赛珍珠的认识也包含有这一层的意思。中国学者一般依据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观点,认为西方的文学作品是模仿生活的实录式现实主义的作品。谁知赛珍珠竟说“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而且“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还赞扬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赛珍珠的中国小说观公允通达,也使我们了解到西方对中国小说的正反两种评价。赛珍珠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高度肯定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不同的特殊表现形式。她是在正确理解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因而她的论证是可靠的。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以上评价与她学习中国古典小说、从事创作的艺术实践是一致的,处处闪耀着辩证思想的动人光芒。
赛珍珠具有敏锐的辩证思维,除了她具备渊博的中西文化的学问、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宽广的文化胸怀、有志于中西文化的互补和交融外,还与她自幼在华处于“异乡人”的身份有关。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首创“异乡人”(stranger,又译作“外乡人”)的概念,其定义是:“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忘却来去的自由。”齐美尔又指出,在“异乡人”身上,体现了人际关系中远与近的统一;关系中所蕴涵的距离,表明近在身旁的人,是遥远的,而这种外来性,又表明遥远的人却在眼前。异乡人对寄居国及其人民的观察和评论具有人所不及的客观性。
仲鑫曾指出,赛珍珠自幼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说中国话,听中国故事,看中国小说,上中国先生的课,玩中国的游戏,还熟悉中国的民俗,甚至会用中国国骂。但她保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接受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念,是地道的美国人。她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也懂得中国的思维方式,她又精通西方文化艺术,使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和写作。这便是赛珍珠作为“异乡人”在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的远与近的统一,这对她的辩证思想的形成,极为有利。我们更应看到,赛珍珠作为异乡人,既具有局外人避免当局者迷从而态度比较客观的优势,又在主观上带有热爱中国及其人民的极大热情,她在创作和论说中对中国种种人物和事物的描写和评价,便是这种主观和客观结合的辩证思维的杰出产物。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相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