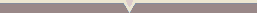笔者三代以来生活在镇江,我发现,上文的两处书场(黑桥、五十三坡),都与赛家在镇江的两处住所(五十三坡书场紧邻就是当时英美领事馆,今镇江博物馆)靠得很近,尤其是黑桥附近的露天书场,印证刘龙先生对赛珍珠回忆“打谷场上听敲铜锣的说书艺人讲故事是终生难忘的趣事”的考证(打谷场在其旧居不远处,见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第2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周边居民中也多“两淮”逃荒来的移民,特别是1905年淮河水灾,灾民顺运河到镇江,麇集在宝盖山、云台山、镇屏山一带(津沪铁路修建宝盖山隧道时,曾以工代赈,招募了许多苏北逃难人员),因此镇江的苏北人口比例骤增,他们的文化娱乐主要是看淮剧、听淮书。
地道的镇江人、扬州人自恃文化品位“高于”清淮一带(即指清江、淮安,现在淮安市的4区范围),不听淮书的,认为有失身份笔者认为,揆其原因有移民原因、经济原因,如清初以来扬州人口多为徽州移民;也有灾害原因,明朝中叶,黄河决口,水入淮河,决高家堰,哀鸿遍野,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笔者幼年就听爱听扬州评话的祖父带有歧视性地说那些淮安人说的“小书”、“下三流书”,说这些书是说给“苏北扛大包”或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的,他们甚至侮辱淮安等地的苏北为“淮刁”和“下河貉子”。这里举个例子:在上海务工的扬州理发师周殿元追述“1949年以前,我们到太原坊去听扬剧,听众全是扬州人,特别是理发师。但我们从不去听淮剧”,从文化活动反映了扬州人的地方主义。(〔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和上述镇、扬人不听“淮书”同出一辙。
道光间邗上蒙人《风月梦》(胡适在《扬州的小曲》说“此书写扬州妓女生活,颇能写实,可以考见乱前的扬州的风俗”)第二回:“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玩。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清末汪有泰的扬州竹枝词说“把戏淮书杂色多”。民初孔剑秋有竹枝词:“一段淮书唱不休,盲词瞎语诌春秋。儿童爱听无稽语,拍马无端闯上楼。”直接将淮书鼓词等同于“瞽词”——瞎说。可见扬州文人对说淮书描述的态度也不好,他们觉得淮书是一种戏谑、荒诞、恣肆的“据地为场,敲锣击鼓,信口雌黄,大抵无稽之言居多,听者士大夫无一焉”的下乘说书技艺。(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广陵书社2002年版,第49页)
淮书艺术在各地
淮书是民间曲艺品种,却不见于辞书以及《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协上海分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淮书”与苏州评弹、扬州评话一样,是一种说书艺术,流行于晚清、民国。生于扬州的镇江籍陈汝衡教授在《说书小史》(中华书局)中说:“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名称是‘说淮书’,也是一种鼓词。”胡士莹在《宛春杂著》里谈及“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故称其技为“说淮书”。淮书在近代知名度不算低,据扬州学者韦明铧研究:大约一百年前“无论在江淮,在江浙,甚至在四川,都常常可以看见那些敲着小锣小鼓,操着淮腔淮调说书卖唱的流浪艺人。这些艺人被称作说淮书的”。
安徽寿州李警众《破涕录》中写道:“盲翁负鼓,信口开河,名曰说淮书。其言荒诞不经,实有令人闻而失笑者”。作家阿英在《小说闲谈·杂考四题·说书篇》中对于淮书记载不同于扬州的描述:“……湖南的‘讲评’,在我们家乡也有,不过那是指在茶馆里说书而言。至于在大的书场上说书的人,一般的却叫做‘说淮书’,因为说书的人,大都是由淮河以北而来。说书的中心地点,是‘把戏场’一带。”阿英是安徽芜湖人,他描述的淮书是在接近淮安的芜湖一带流传的情况,可能是淮书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境况吧。今天淮书艺术已经消亡,虽在淮地,也罕为人知。
淮扬曲艺的影响
赛珍珠从童年开始,对评话、弹词、鼓词等口头文学兴趣很浓,她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终了说:“村屋里的说书的人,文人经过时他无需抬高他的嗓子。但若一群上山求神朝圣的穷人路过时,他一定要使劲把他的鼓敲响。”(刘龙:《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这里的说书人倒像淮书艺人。赛珍珠对“淮书”应该有些模糊印象,可能与赛家在清江浦的短暂生活经历或镇江寓所附近很多的淮安、清江人士有关(直到现在,镇江城区务工人员中首推淮安人,近90万人口的市区号称10万“老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