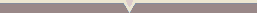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心理中他者的幻影。它可能出现在文艺作品中,也可能出现在新闻报道甚至严肃的论著中。同一时代不同类型的文本,以不同的方式,协调构筑同一个中国形象,事实上谁都没有真正地解释中国事实,而是在解释西方文化他者想象中的欲望或恐怖。20世纪初,由移民潮与义和团造成的黄祸恐慌过去了,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让西方人感到安全,于是,各种离奇和好的想象联翩而来,哲学家们开始像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先辈那样引用中国同行的话,只是老子、庄子比孔子更重要了。启蒙哲学家引用孔子要入世,罗素、杜威、凯塞林等等引用老子、庄子要劝急功近利的西方人出世一些。哲学家的教训经常让大众感到不知所云。他们分不清陈查理嘴里引用的那种听起来像古怪可笑的陈辞滥调的“孔夫子的格言”,与哲学家引用的那些"语录"之间的什么区别。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的中国想象的,是文学。《大地》出现了,不仅为西方大众找到了合乎时代口味的中国形象,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地》具有划时代性。但1931年才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1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国形象一直朝正面发展。而且不久参与构筑这一正面的中国形象的文本,就从文学铺展到各类新闻报道、学术著作,尽管在虚构这一点上,它们都还是“文学”。这些文本的广泛传媒,在西方大众间掀起了继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又一次大规模的“中国潮”。
20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中国潮”,构成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段“闪亮的日子”。18世纪的“中国潮”的领导在法国,20世纪则在美国。《大地》使那么多西方大众突然间开始关注中国并且产生好感,一改19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鸦片帝国的恶劣印象。它既说明一部作品的社会影响,又说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为作品的产生与流行提供的必要条件。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代表,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被两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精疲力竭,已经无暇顾及中国了。19世纪曾经代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英国,20世纪不仅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上的霸权优势有所减弱,文化霸权的优势也日益让位给美国。法国有优秀的汉学传统 ,但在20世纪前半叶也没有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多少贡献。德国在30年代曾经与蒋介石政权有过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 ,但这种交往并没有影响到大众文化。1935年德国大众关于中国的印象,似乎与1835年差别不大。整个20世纪前半叶,似乎只有美国文化,对中国抱着某种浓厚的兴趣,而且美国的中国形象,也影响到欧洲,就像《大地》的电影与小说同样风靡欧洲一样。
四
20世纪的美国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中国情结"。这种中国情结可以解释傅满洲、陈查理,也可以解释《大地》或《时代》杂志上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20世纪的美国有一种“中央帝国”的心态。英国在19世纪自觉到“拯救”印度,美国在20世纪自觉到“拯救”中国。如果沿着美国的拓疆线路发展,从中西部到西海岸,从西海岸到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1898年占领菲律宾后,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另一边的中国了,而义和团事件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一直把美国军队送到北京。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这是最富刺激性的拓疆想象。像西方扩张的以往历史上发生的那样,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先驱,仍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财富的市场,传教士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灵魂的市场。在商人与传教士之后,必然跟进的是政客与军人。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希望改造中国,并以同样的信心坚信中国将被改造成一个顺从并感激美国的经济上开放、文化上基督教化、政治上民主的美国式的“藩属国”。千年之后的美国像千年之前的中国,理想的世纪秩序是八方向化,四夷来朝。
美国的“中央帝国”心态使美国对中国,这个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中国与美国有同样大的领土,有五倍于美国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正处于某种权力空洞的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尝试在这位土地上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只在那里制造了混乱而不是秩序。20世纪该美国出场了。“到1899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的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在东太平洋和在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 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新边疆,地球上一块最有吸引力也最有危险,因而最富挑战性的地方。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矛盾复杂,经常是爱恨交加,恩威并施。一方面是“黄祸”恐慌,使他们惧怕、仇视、打击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恩抚主义”(Paternalism),使他们关心、爱护、援助中国,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成熟、多少有些弱智低能,也多少有些善良人性的半文明或半野蛮国家。在中国身上,美国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从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中,感觉到自己的重要与尊严。杰斯普森(Christopher Jespersen)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曾详细分析过美国对中国的矛盾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中体现出的美国对自身中央帝国位置的认同过程。“从19世纪最后10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建立在两种强有力但又相应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A.贺伯逊所说的上帝与玛门(指财神--引者注)或‘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上……美国的中国观的第二种冲动与前一种对中国进行精神与经济拯救的诱惑完全相反,第二种冲动集中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最终导致排华法案……美国的中国观从基督教恩抚主义到经济开发热情一直到种族主义偏见,融合了不同的态度、期待、希望、彼此之间甚至完全相反。” 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排除了黄祸恐慌,到2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种在精神与经济上“拯救”中国的冲动占了上峰。尽管这种“拯救”的真实意义令人怀疑,就像孔华润指出的:“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 其实这也是所有西方势力试图拯救中国的共有逻辑。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研究西方3个多世纪援助改造中国的活动时指出:“这些活动背后的内在动机隐曲复杂,他们的真实欲望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帮助他们自己。”